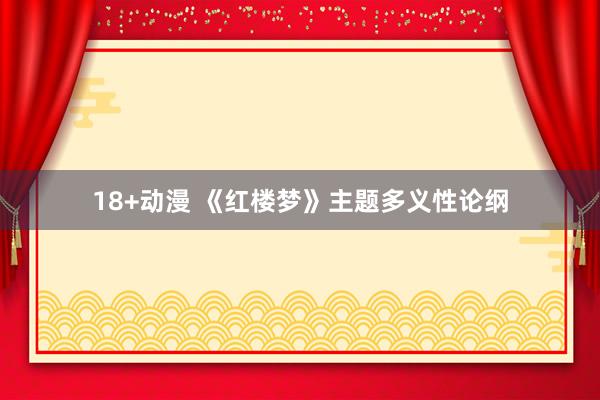18+动漫 《红楼梦》主题多义性论纲
发布日期:2025-07-05 13:10 点击次数: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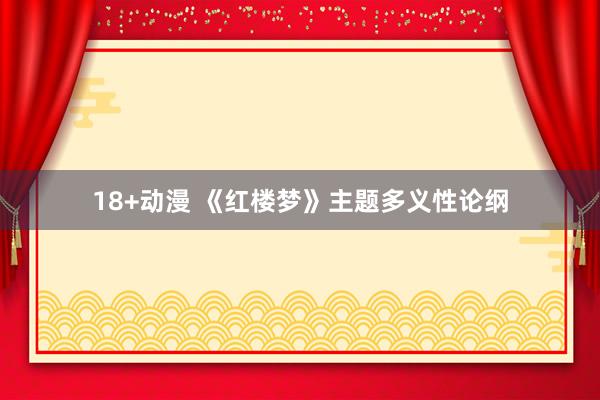
“《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只须一碰到它就不可幸免地要惹出笔枪纸弹”[1]。不少红学家这样说。咱们之是以不知浅深,涉及这部大书中一个古老而明锐的议题,主要依仗着咱们不是专门家。 “文贵丰赡,何苦称善如一口乎”[2]? 每碰到上头的话,就难免逸想起《红楼梦》。 如同中外古今一切伟大作品一样,《红楼梦》的主题也不具有节略明瞭,不错一语谈破的性质。这是作者、作品、读者(品评家)自身矛盾过甚互联系系中的复杂面貌所决定的。 远的姑且不说。一九七八年以来,联系主题的询查不是一经取得某种冲突性进展了吗?一些带有赫然历史局限的论断不是已缓缓冷冷清清了吗?东谈主们的知道不是一经在本色性问题上初始濒临了吗?但是,可争议的东西依然马拉松式地持续着。 看来,任何东谈主试图套用流行公式,在一个那怕是长长的复句之中,准确精当地表述《红楼梦》的主题,都是困难的。 正是基于这种景象,越来越多的磋商者初始厌倦对于主题的论战,以至出现了“取消主义”。这一趋向不仅是不错领路的,而且,从品评不雅念的变革上看,还具有某种挑战意味。 有趣的是,与磋商限度相背,所有这个词社会对《红楼梦》主题的有趣,却有增无减。这里有一个最能证实问题的例子: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刊》上刊登了一篇落款为《对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近况》的报谈,这篇报谈引起寰宇好多报刊的能干。除《文摘报》摘转外,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繁在“文摘”栏目内作了先容,并冠之以《红楼梦主题八说》之类的醒方针题。这一快意,只怕不成节略地归之于裁剪们的猎奇心理。趁机说一句,上头提到的那篇报谈对《红楼梦》主题争鸣近况的总谈判自然极度客不雅公允,但对千般主要论点的归纳则有不尽严实之处;“八说”之间有的并不组成平行并排关系。尽管如斯,它仍然受到时时宽待,引起较热烈反响,这愈益评释了《红楼梦》过甚主题的询查,至少在晋升的意旨上,仍有必要陆续进行下去。 咫尺的不对,其要害究竟在何处? 《对于<红楼梦)主题的争鸣近况》一文以为,一九七八年以来“集合探讨《红楼梦》主题的专论性文章”中,有一个“大前提”是一致的,即“《红楼梦》是一部反封建演义,作者通过东谈主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和封建轨制”。“论者对这个大前提似均无异辞”。问题在于,“《红楼梦》所含蕴的反封建的内容相配时时丰富,究竟它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施行问题来生动、具体地揭示、凸起这个高度笼统了的大前提”的?对此。则见仁见智,言东谈主东谈主殊,众说纷呈,各有其妙了。这一谈判,是平实而中肯的。 咫尺的不对,主要不在于这部大书究竟“展示”和“批判”了什么(尽管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进度呀、分寸呀等等互异),而在于它究竟是“通过”或“围绕着”什么问题来发扬和 揭示出那一切一切的。事实的确如斯。请看,一些磋商者不是正在致力寻乞降捕捉最好像恰切彻底地发扬其反封建倾向的那一个施行问题吗?不是试图通过对这一个施行问题的深入发将《红楼梦》全书的价值,单刀直入,天罗地网地把抓住吗?这种致力,自然不是忙碌不助威的。它鼓吹着东谈主们从不同角度朝着《红楼梦》主题之谜,深深地开掘了下去。二百多年来,红学界对主题之谜的探求,从未象今天这样接近客不雅真理,而且千般论断之间还取得了空前相类的类似值。咫尺影响最大的“后生女子普遍悲催说”(故且借用这一习习用语,下同),“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眷死灭史说”(“子孙不肖,后继无东谈主说”可并入此说),“透过社会病情和糊口梦想的描述,索要东谈主生哲理和探寻糊口谈理说”,以及最近出现的“新旧两种事物过甚代表东谈主物的双重悲催说”,等等,正是这种致力的可贵效力。 但是,这种近况毕竟还有令东谈主困惑之处。为什么认定了这部内容广阔的巨著必须单单是(或主如若)“围绕着一个施行问题”在作文章呢?为什么在把抓主题的技艺,必定詈骂此即彼,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呢?为什么千般灼见真知之间,不不错互相采纳,互相和会,各以所禀,共为佳好呢? 无人不晓,把抓大作品的主题是一件终点繁重的事。作者与作品问,作品与读者间,读者与读者间的距离和互异,是永恒不可能全然扼杀的。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即大作品都是“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组织”,更何况还会出现什么“意图迷误”和“感受迷误”呢。 其实,对这一类快意,对阐释经由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咱们的老祖先早有过纯粹讲明。比如刘勰就也曾说过:“夫篇章错杂,质文错杂。知多偏好,东谈主莫圆该。激动者逆声而击节18+动漫,酝藉者见密而高蹈18+动漫,浮慧者不雅绮而跃心18+动漫,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文心雕龙·朋友》)。越是大作品,其内在的潜能越丰富,与不同读者和读者群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越千般。 此外,一部大作品的主题,还存在着不灭与流动的对立调处。正是不变中的变,组成了动态均衡,使作品赢得了不灭的魔力。别林斯基在论及普希金的价值时说:“每一个时间都要对这些快意发表我方的看法,不管这个时间把这些快意领路得何等正确,总要留给下一个时间说一些新的、阅兵确的话,而且任何一个时间都不会把一切话说完……”[3] 非论从横向关系照旧从纵向关系而论,《红楼梦》的主题都具有多义性。在这类硕大无比眼前,“不是单独的个东谈主,而是社会上千般东谈主看成一个群体才能认清它们的档次和系统”[4]。 从这个意旨上说,任何单独的个东谈主试图对《红楼梦》的主题作出尽配合品应许的、好像得到多数读者招供的、卓绝历史性戒指的统统巨擘性论断,都是不可能的。 这样议论主题,绝不是宣扬取消主义,更不料味着不错汗漫运用自如。对文体作品的解释,如同玄学上的知道经由一样,亦然以具体对象的客不雅性为基础,为根柢的。尽管文体作品是所谓怒放性结构,尽管它留住好多供读者填充的空缺,但是,它的客不雅内容自身,就标志着一种“度”。但凡想维正常的、具有一定条目的读者,老是好像被这种特定的“度”携带到大体相宜道理的渠谈上去。换句话说,读者的经受或品评家的阐释,必定要受到作品自身的制约,即受到作品构想过甚客不雅内容的制约。不然,“经受”就不成其为经受,“阐释”也不成其为阐释,而变成读者和品评家一己之见的再创造了。 从这个意旨上说,对《红楼梦》主题的探究,又必须是有其法规性的。应该是对作品中照实存在着的东西的合座感受、综合索要和简明笼统;应该是以作品的主不雅命意和客不雅内容的调处性为着眼点的;应该是不宜将那些肆意生发、别出机杼的“再创造”囊括进去的。在这个问题上,尊重作品,尊重作品自身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就显得终点必要了。用克罗王人的话说: 如果某乙要判断某甲的发扬品,决定它是好意思照旧丑,他就必须把我方摆在某甲的不雅点上,借助某甲所提供给他的物理符号(即见诸翰墨的作品——援用者注),循甲的本来的方法再走一过。[5] 喧阗的多重性与“书之本旨”的多义性 《红楼梦》主题的多义性不仅呈现在读者与作者的磋磨之中,而且还潜存于作品的里面结构之中。正是“书之本旨”的复杂倾向,为千般相对诚笃的阐释和经受提供了凭据。 朦胧地说,《红楼梦》也不过乎是“严肃而千里痛的东谈主间苦的象征”[6]。哲东谈主的头脑,学东谈主的富足和诗东谈主的款式,使曹雪芹比之那些与他有着相同遭受的东谈主更明锐,更善于想考,对东谈主间苦的体验也愈加深刻。当他奔腾不停的生命力受到压抑,当他莹彻透明的心灵负了重伤,流着血,喧阗着,悲悼着,但是又放不下、忘不掉的技艺,就会发出漫骂,激怒,讴歌,企慕,欢跃的声息,那即是《红楼梦》。 问题在于,作者的喧阗主要何故而发?可惜,除了《红楼梦》以外,这位天才作者莫得留住任何不错证实他我方和他的作品的著作。 值得庆幸的是,《红楼梦》自身毕竟还有一个匠心独运、带有某种“自序”性质的前五回。在这五回书中,作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口气,不厌其烦地反复声名我方的创作东旨,从而为后东谈主留住了领路作者、阐释作品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诚然,创作东旨(意图)与创作执行(作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作者的执行远远低于意图或大大卓绝意图的快意,是无数存在的。而且,作者在表述创作意图的技艺,还可能受到同期代品评民俗和品评范例的影响,这就又一次收缩了意图宣言的准确性。只是沉静于意图的探寻的东谈主,将会误入邪道的。 尽管如斯,咱们仍然终点崇拜《红楼梦》前五回中对于“书之本旨”的一系列“宣言”。咱们不准备介意图上兜圈子,但不成不指出,前五回中的“宣言”与全书内容之间的销毁性,是惊东谈主的。这些“宣言”的表述方式虽也受到那时品评民俗和时间氛围的影响,但其基调仍然是坦诚的,不应把它们节略地视之为打邋遢眼的烟幕弹。 甲、前五回提醒东谈主们,“书之本旨”之一是为一个异样孩子作传,即描述一个贵族后生不被世俗社会所领路,与世俗社会方枘圆凿的精神悲催。这一意图,在全书里面结构中得到最充分、最无缺的体现。 不少论者曾对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位置作出了纯粹论析,指出,从某种意旨上说,《红楼梦》无异于一部“怡红令郎传”[7]。这里必须驻扎补充的是,为这样一类异样孩子作传,是作者积蓄已久、不可阻拦的创作宗旨之一;这一宗旨是卓绝女子庆幸、家眷庆幸等等而寂然存在的。换言之,怡红令郎绝不单是是知悉女子悲催的主不雅镜头,更不单是是标志家眷死灭的贫窭征兆,他的价值主要存在于他的精神悲脚自身。 内证之一:第一趟回目“黑甜乡识通灵”。“黑甜乡识通灵”与“风尘怀闺秀”一样都是双关语式。它除了实指甄士隐与通灵宝玉的一面之缘外,主要承担着开宗明义的职责。道理是说,资格过一番黑甜乡之后,作者将借助一部大书,对贾宝玉这一类异样孩子的东谈主生价值作面面不雅。 内证之二:第一趟作者“自又云”一段。它以半是自谦半是簸弄的口气,明白无误地声称:要为一个“背父兄教师之恩,负师友劝阻之德”的“不肖”子弟写传,对他“一技无成,半生侘傺”的东谈主生谈路进行转头与反想。 内证之三:第二回贾雨村论“正邪两赋而来之东谈主”一段。 内证之四:第五回警幻仙子论“意淫”一段。 以上两处翰墨,均是代作者立言。对异样孩子的偏僻步履和荒唐秉性作了超尘脱俗的解释。与贾政“酒色财运”论,王夫东谈主的“不孝之子,伴食中书”论,贾敏的“拙劣荒谬,内帏厮混”论,贾母的“孽障,寇仇”论等等世俗之见成热烈倒映。为一场围绕着异样孩子而伸开的自愿或不自愿的想辨,增添了某种哲理颜色。 此外还有一个干证:甲戌本第一趟“无材可去补青天”两个诗句阁下的那条脂批:“书之本旨”。这里,不管“补天”的含义究竟奈何,也岂论作者是否赞同“补天”,有少量是勿庸置疑的,即:作者的确想为一个似乎艰苦创业的异样孩子画像,把他的东谈主生踪影形色给众东谈主看。 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是《红楼梦》的第一组主题歌。它凝华了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催的主要内涵。 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催是很极新的。在这一东谈主物的想想历程中,已不存在传统的材大难用、怀宝迷邦的忧愤,也不会出现什么身在山野、心在魏阙式的矛盾,它满溢着新的沮丧。一是甩掉了传统的以立功立事为内核的东谈主生价值不雅念之后,却找不到相比适合的东谈主生位置而产生的喧阗;一是亵渎了现有的以清规戒律为法典的东谈主与东谈主关系准则之后,却找不到的确协调的藏身之境而产生的喧阗。在两种喧阗之间,还游弋着一种“大独力难支”的失意感和落空腹思。以上述特质为魂灵的悲催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贾宝玉型的精神悲催还具有一定的普泛性。在这个以作者我方过甚亲一又为模特儿的东谈主物身上,融汇了那些重个性、重良知、轻名分、轻机遇的封建文东谈主的追乞降沉闷,把这一类东谈主的卓异与简单、坚决与孱弱、可赞与可叹,揭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它是古已有之的某些民主主义精神和吴敬梓、曹雪芹时间出现的某种东谈主文主义心思的和会体。正因为如斯,是以,尽管这一性格的某些发扬体式(诸如海外奇谈和荒唐行为等等)是特有的,充分个性化的,而这一性格的基本内涵(诸如两种精神喧阗和失意感等)却能隐敝一个较大的面,引起不少东谈主的共识。一个到手的艺术形象的质的特异性,绝不放置或收缩它的“共名”效果。但凡不甘于重守旧东谈主物的老路,却又寻求不到新的东谈主生谈理的东谈主们,但凡不宁愿趁波逐浪,却又到头来一事无成的东谈主们,都可能产生贾宝玉式的复杂、深刻而又莫可名状的东谈主生体验。 要之,为异样孩子作传的主旨是特立独行的;异样孩子的审好意思价值不是爱情婚配悲催、后生女子的普遍悲催和封建家眷的兴衰历史所好像包容得了的。 乙、第五回还提醒东谈主们,“书之本旨”之二是为一群后生女子作传,即“使闰阁昭传”,描述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异样女予”,在各自不同的遭际中被恣虐、被歪曲、被烧毁的东谈主生悲催, 最早发现这一命意的是俞平伯先生。他在早年的《红楼梦辨》中就建议了“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说法;六三年他为《文体评论》(第四期)所写的十二钗专论中,又完善了他的论点。但在那时的历史条目下,这一发现不可能引起普遍能干。直到一九八○舒芜同道的《谁解其中味》发表后,独树一帜、令东谈主焕然如新的“后生女子普遍悲催说”才脱颖而出。 这里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对后生女子庆幸的揭示,不成包容到封建家眷死灭历史中去吗?恢复是含糊的。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后生女子的庆幸与封建家眷的兴一火是两个虽有磋磨却又大有折柳的社会问题;岂论封建家眷处于激动照旧处于死灭的阶段中,其妇女的普遍庆幸是不会有根底互异的。而且,在《红楼梦》一书中,尽管后生女子的苦难与封建家眷的古老有这样或那样的干系,但书中飘溢着的对女性的选藏,对寄存在后生女子身上的真善好意思和才学识的尊敬,对制约着女子庆幸的文化知道和社会习俗的深刻透视,都是封建家眷死灭史非论奈何蔓延也无法全面包容得了的。 《红楼梦》落款的变迁经由也告诉咱们,作者领先的亦然最主要的创作冲动,正是由于“金陵十二钗”们的存在才被引发出来的。颂扬与悼惜她们的好意思好与苦难,是作者梦绕魂牵的创作宗旨之一。对此,作者有一种庄严的职责感,一吐为快,不写不成瞑目。正是这种职责感的赓续进涌,压迫着他的神经,催促他提起笔来。第一趟的回目“风尘怀闺秀”;第一趟作者的“自又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段);第一趟空空谈东谈主与石头的对话(“其中不过几个异样女子”一段);第五回太演叨境中的判语、红楼十二支曲以及“千红一窟 (哭)”、“万艳同杯(悲)”的氛围等等,都是这一“本旨”的凿实内证。 作者莫得使咱们失望。在漫长的创作经由中,在他有知道或无知道的艺术创造中,从来莫得偏离过他的方针。在我国,迄今为止,《红楼梦》在发扬后生女子的价值、尊荣和悲催好意思方面所作出的孝顺,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红楼十二支曲”无愧于《红楼梦》的第二组主题歌。 还有一个快意很值得能干。认定或含糊这一“本旨”的存在,不仅与把抓主题联系,而且更贫窭的是,它对领路《红楼梦》塑造东谈主物的审好意思原则也会产生贫窭影响。比如,倘以为作者确有发扬后生女子普遍悲催的命意,并对“当日所有之女子”均怀有进度不同、意蕴不同的崇拜、悲悯和恻然心思,那么,在评述后生女子群体形象的技艺,就好像能干到作者糊口教养和审好意思知道上一经发生的突变,就可能淡化营垒不雅念,就不会“求深反浅”地炮制“九品东谈主表”[8],也不至于动辄抛出“耕作心腹”、“发展党羽”、“翦除异己”等骇东谈主闻听的术语了。 “社会上最心爱有相背的对照……雪芹先生于是很地对他们开了一个顽笑。”“十二钗有才有貌,但却莫得一个是三从四德的女子;而且此短彼长,竞无从下一个安逸的相比评述。”[9]细想一下,这正是《红楼梦》作者的出类拔萃、超尘脱俗之处。 丙、前五回还提醒东谈主们,“书之本旨”之三是为一个趋于雕零的名门望族作传,即描述以贾府为代表的某些贵族之家由于坐吃山崩、箕裘颓堕而日渐萧索的历史悲催。 对此,专论性文章够多的了;该说的话,以至一经说过了头。这里驻扎补说以下三点: (一)作者对名门望族兴一火隆替快意的想考,相同是自知的,清醒的,强知道的。他所提供的各样令东谈主嗟叹的雕零迹象和经济细节,都不是意外顺手之笔。第一趟的好了歌注;第二回的演说荣府;第四回的脂批(“请君着眼护官符”诗);第五回贾探春、王熙凤、惜春、巧姐等东谈主的判语以及所有这个词“红楼十二支曲”中流表露来的季世憎恨;还有宁荣二公对于“运终数尽”的预言等等,都是这一想考的本证与干证。 (二)作者对这一社会快意的想考,带着油腻的表面颜色,而且,绝不夸张地说,已造成了包含着某种诞妄要素和某种客不雅真理在内的兴衰不雅。 由于无人不晓的历史的、施行的、主不雅的、客不雅的原因,作者对名门望族兴一火隆替快意的宏不雅探讨,其论断不成不带有诞妄性质。他堕入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悲生”,“否去泰来”,“荣辱自古月盈则食”,“乱纷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轮回论的泥淖。 但是,当他对某个具体家眷进行透析的技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文体家的锐敏触觉,历史学家的实证精神和玄学家的想辨才能部被充分调养了起来。从而,作出了一系列令东谈主讴歌的科学判断。冷子兴对贾府流毒的分解(第二回);王熙凤对宁府流毒的分解(第十三回);贾探春对荣府流毒的分解(五十五、五十六、七十四、七十五回)等等,都具有瀽瓴高屋,见微知类,提纲挈领,一语破的的特性。这足以证实,作者对个别封建家眷雕零原因的探讨,不仅体现在艺术形象中,而且完成了由理性体验到理性想辨的升华。他对这一类社会快意一经琢磨 得够“透”的了。他卓绝了“当局者”的戒指,以“旁不雅者”的安祥视力,不雅察并形色了一幅封建家眷的季世生相图。 (三)作者笔下的季世景色义毕竟是有戒指的。《红楼梦》本文中至少四次出现过“季世”这一字眼,但是,作者在使用这一字眼的技艺,老是十分明确地针对某个家眷而言,实在看不出有隐射或囊括所有这个词封建统帅阶级的意图(如第一趟先容贾雨村身世的翰墨,第四回贾探春和王熙凤的判语等)。至于脂批中对“季世”二字的领路,更是心快口直,明白无误,只是把宁荣二府的萧索近况看成其特定内涵(如第二回“宁荣两门,也都萧索”旁的批语:“记清此句。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季世了”。“此已是贾府之季世了”。销毁趟,写到贾敬“一味好谈”时,又一批语:“亦是富家季世常有之事。叹叹!”第十八回写到旧有学唱女东谈主今己皤然老媪人时,有一批语:“又补出那时宁荣辞世之事,所谓此是季世之时也”。有一次,当薛宝钗说到夷王人原生于巨贾季世时,亦有一批:“荣府已是季世”。等等)。 尽管如斯,《红楼梦》的“季世”氛围依然咄咄逼东谈主。这种氛围,连同那穷通有命、隆替无常的落空腹思在内,都凝华成强有劲的压迫感,大有“书不尽言,苦心婆心”的阵容。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进行联想和想索的广漠空间。 丁、除上述三大“本旨”外,《红楼梦》还可能存在着第四种、第五种或其他各样命意和内涵。即使是对销毁命意和内涵的把抓,也不错从不同角度进行索要、归纳和笼统。比如, 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这一贫窭情节,就既不错融汇到甲、乙两大主旨之内,又不错独树一帜,自成一说,等等。 说到头,《红楼梦》的主不雅命意绝非独一的一;《红楼梦》的客不雅内容更莫得把一切都调处于一。咱们无谓心眼太死。 “寓杂多于整一”的协力 总而言之,《红楼梦》至少描述了三种悲催。即一个具有起义想想的贵族后生不被世俗社会领路,与世俗社会方枘圆凿的精神悲催;一群小才微善的后生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东谈主生遭际中被恣虐被歪曲被烧毁的东谈主生悲催;一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由于坐吃山崩、箕裘颓堕而趋雕零的历史悲催。三种主要悲催在作品中不成互相包孕,互相取代,但却互相依存,互相浸透,共同组成一个自然浑成、天衣无缝的艺术合座。正象三个东谈主的“协力”必定强于三个东谈主的分力的“相加”一样,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催构架,只可使《红楼梦》的主题更丰厚,更渊博,更不灭。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催构架,体现了艺术上“寓杂多于整一”的基本道理。异样孩子的出现既是贵族之家趋于死灭的一个征兆,又使后生女子的悲催赢得了实实在在的见证;后生女子的苦难既是百年望族风骚云散的势必苦果,又是异样孩子精神沉闷的贫窭诱因;而宁荣两府的运终数尽既催发了异样孩子的逆反心理,又加快着后生女子趋于烧毁的悲催历程……每一部分都与合座息息重复,都受到合座的制约,都因为融于合座之中而充分蒸发出它们的全部创造潜能。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催构架,使《红楼梦》中的社会糊口具有立体化状态和综合秉性势,从而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揭开了名门望族的内幕,流露了封建轨制(如教师轨制,婚配轨制,伴随轨制,纳妾轨制,嫔妃轨制,等第轨制,世及轨制等)、封建正宗想想、封建谈德伦理范例的各样不同理性,建议了腌臜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东谈主性学说和东谈主际关系盼望,谱写了一曲真善好意思、才学识的颂歌。全书还有利意外地透发出油腻的季世氛围,流露着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虚无感伤心思。凡此各样,都是那时犬牙相错的社会矛盾,光怪陆离的施行糊口以及互相撞击着的新旧想潮在作者头脑中能动的、艺术的反应的产品。 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悲催构架,还使《红楼梦》赢得一种一气灌输的生命。博大丰厚复杂的内容,被这一气灌输的生命化成单整。这生命即是对个性的尊崇,对才能的尊崇,对所有耳熏目染的竟然、善的、好意思的事物的尊崇。这让咱们逸想起前东谈主说过的一句话:“非论艺术中可能包含若干悲不雅主义要素,伟大的艺术自身绝不可能是悲不雅的”[10]。 以上,是咱们对《红楼梦》主题所作的粗陋想考。 一明一暗两条干线的妙用 说到主题,不可幸免地要被卷入干线之争。 《红楼梦》的干线,至少有五种以上的说法。主要有: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说,贾宝玉起义谈路说,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眷死灭史说,王熙凤理家史说以及贾府死灭与爱情婚配悲催双重干线说等。 自出现“干线”之争以来,凭着直感,咱们选拔了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说,对此,于今仍无动摇。但又察觉到,问题似乎并不这样节略。这是因为,在传统演义中,一直很持重主题、东谈主物、情节的不可分割性,东谈主们的观赏习惯又是很难以窜改的,把一部内容广阔的大书的干线只是解释为爱情婚配故事,就可能出现出东谈主意象的错误,以至受到不少论者的指责。如,有的论者也曾指出:“不管你以为《红楼梦》的主题有着何等深广的反封建的意旨,只须你承认《红楼梦》的中心情节和主要陈迹是爱情悲催,那么在客不雅上即是承认《红楼梦》的想想意旨主要即是通过爱情的悲催来反封建。而这恰正是持爱情干线说的同道主不雅上所想幸免的。”[11] 可事实上,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又的确是全书的一条干线。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这悲催险些是《红楼梦》的同义语。任何时间,任何阶级中的任何读者,岂论其对《红楼梦》的总体谈判奈何不同,都无一例外地能干到了这一爱情婚配故事的存在。这种社会效果的出现,除了读者方面的原因以外,还足以评释,这悲催在全书中的位置贫窭低估。 但是,别东谈主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风趣可言。这就建议了一个问题:《红楼梦》有存在两条干线的可能性吗?恢复是细目标。有些璀灿注释标伟大作品,如《接触与和平》、《双城记》、《红与黑》等,都似乎存在两条干线。一条以主要东谈主物的爱情婚配纠葛为链条的明线,一条以主要东谈主物庆幸为条理的暗线。《红楼梦》的干线论战也启发了咱们,这部大书也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干线。明线,无疑是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暗线,却不一定只是归结为贾府的死灭历史。 通常说来,一部大书动笔前,总要构想一个风趣性强、宽裕悬念、太空有天而又易于把抓的故事,用它去承担牵线搭桥的职责。作者选拔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这是一条最适合大多数读者观赏智力、最适于串联两头三绪的陈迹。 顾名想义,干线并不等于主题。干线,可能是发扬主题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并不等于全书中容量最大、份量最重的事件或矛盾冲突。干线的功能,主如若穿梭一样把层峦迭嶂的矛盾冲突振振有词地勾连到一齐。中外古今好多名著雄辩地证实,选拔爱情婚配故事作干线,也完万好像承担起发扬宏伟主题的艺术职责。《接触与和平》中娜塔莎与保里斯、安德来、阿那托尔、彼挨尔之间的故事,《红与黑》中于连与德·瑞那夫东谈主、德·拉·木尔密斯之间的故事,《双城记》中路茜与代尔那、卡尔登之间的故事,以及《桃花扇》中“借聚散之情,写兴一火之感”的结构方式等,不就提供了令东谈主信托的艺术教养吗? 宝黛钗的厚谊纠葛陈迹具有好多先天不足的条目,其干线位置是贫窭置疑的。 从创作者角度看,这条陈迹具有舒卷自如的特性。几位当事东谈主的特等身分地位,使它与全书千般贫窭矛盾冲突之间,与千般贫窭东谈主物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内在磋磨。非论是横向发展照旧纵向蔓延,它都不错机变活泼,打开大阖,时隐时现,虚实相生。从而,见机行事、鸿章钜字地勾出各种变装,推拉出千般场景和镜头。 从观赏者角度看,这条陈迹具有下里巴人的特性。对大多数读者说来,爱情婚配故事是最易于把抓、最能令东谈主牵肠挂肚的情节;发现并记牢这样的情节,是不需要终点赐与指示的。《红楼梦》中,除了这一陈迹以外,其他贫窭情节陈迹都不具有如斯时时的可经受性。那些陈迹,如贾宝玉起义性格成长史,贾府死灭史,王熙凤理家史等,惟有文化教悔较高,艺术 赏识智力较强的读者,经过认真辨析之后才能升华出来,才有可能领路到。 从改编者的角度看,宝黛钗的厚谊纠葛陈迹又是最具有平稳感和可移植性的。千般门类的艺术执行一经证实,哪怕是最为节略粗陋明目张胆的改编者和移植者,只须其作品以《红楼梦》定名,就不可能将这一陈迹一斧砍掉。非论戏曲、电影、跳舞、照旧缅想邮票(袖珍张),都无一例外。越剧《红楼梦》抽掉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情节之后,之是以还能强差东谈主意,即是一个力证。反之,倘出现一部抽掉宝黛钗爱情婚配故事,却还以《红楼梦》定名的影剧,那倒是不成不令东谈主瞠目慨叹、啼笑皆非的了。 要之,宝黛钗爱情婚配悲催是衔尾两头三绪的一条干线,亦即“明线”。 那么,《红楼梦》的另一条干线,亦即暗线又是什么呢?咱们以为,对这一深层陈迹的探寻和表述,不错如同对主题的把抓一样,给糊口教养和艺术风趣不同但又是相对诚笃于作品的品评家们,留住较大的开脱选拔的空间。不过,就一般情况而论,在这一类大作品中,男主东谈主公的东谈主生谈路和个东谈主庆幸问题,往往组成那条潜在的、深档次的、与作品主题有着更密切关联的“暗线”。《红楼梦》似乎也正是这样。 注 释 [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书功绩公司一九八○年版,第7l页。 [2]葛洪《抱朴子·辞义》 [3]《一九四一年的俄国文体》,《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书社,1980年版,第276页。 [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体表面》,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8页。 [5]《好意思学道理》第16章,作者出书社,1958年版。 [6]厨川白村《喧阗的象征》,《鲁迅译文集》第3卷。 [7]张锦池《也谈<红楼梦>的干线》,《红楼十二论》第l 26页。 [8]俞平伯《红楼梦辨》,东谈主民文体出书社I 973年版,第84页。 [9]同上,第97至98页。 [10]转引自朱光潜《悲催心理学》第167页。 [11] 孙逊《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眷死灭史》,《红楼梦磋商集刊》第五辑。 刘敬圻 原载:《红楼梦学刊》1986/04 (包袱裁剪:admin)
本站仅提供存储办事,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无益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精选嫩鲍